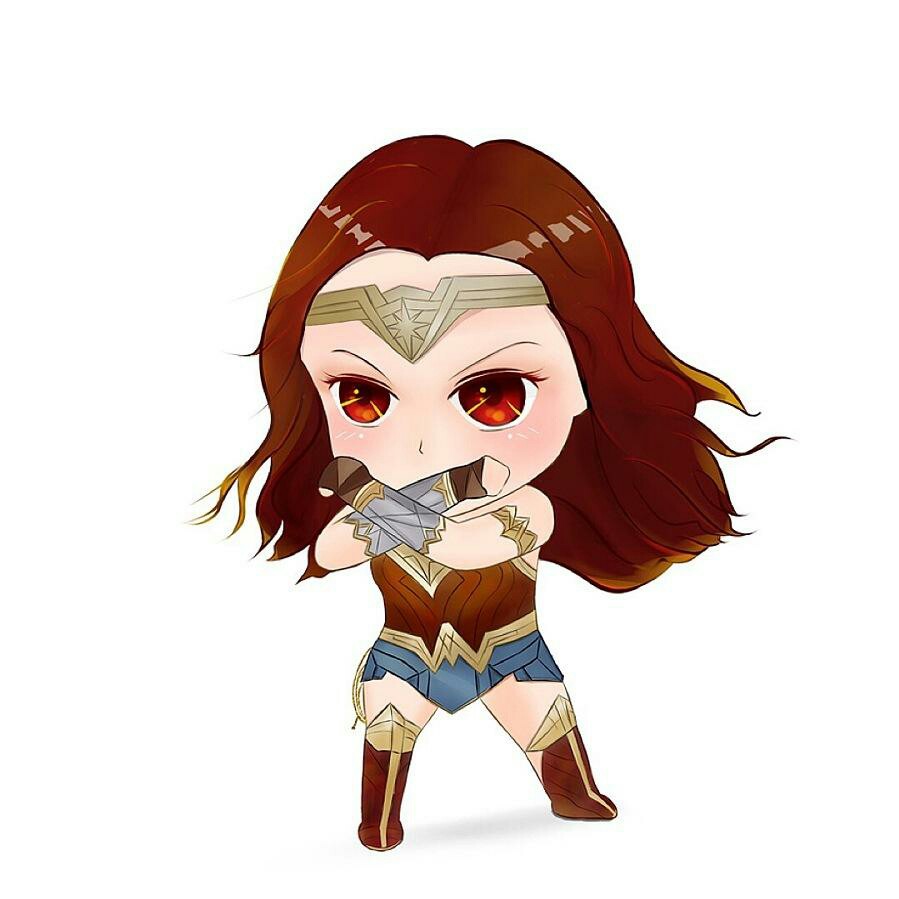從NFT、Meme和CC0的三元融合出發,探討為什麼Mfers會風靡?
原文來源:The SeeDAO
原文來源:The SeeDAO
原文來源:The SeeDAO
二級標題
圖片描述
二級標題
Mfers:連官方twitter都沒有的CC0項目
Mfers是由藝術創作者sartoshi手繪而成的PFP(頭像類)項目,其畫風是極簡的火柴人形象。作為項目的創始人,sartoshi本身是CryptoPunks社區的OG,在NFT圈具有很好的影響力。而項目的技術開發則由Westcoastnft完成,後者也是Doodles的技術開發團隊。
Mfers是典型的CC0項目,即作者對項目僅保留署名權。 “CC”是“creative commons”的簡寫,用以規定與該作品有關的一系列權限。 CC0意味著“No Rights Reserved”,作品被創作者不加保留地放置在一個公共領域,所有人可以自由複制、傳播、進行二次創作等。這種概念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出現了。
Figure 2 | OpenSea TOP NFTs(截至2月26日)
圖片描述
Figure 2 | OpenSea TOP NFTs(截至2月26日)
風頭正盛的NFT項目還有3Landers,它也是一個PFP項目。在Opensea的7天交易排行榜上,3Landers的交易量力壓群雄,穩穩佔據著第一名。與Mfers相同,3Landers也發布了NFT作品的CC0聲明。
同為CC0-NFT的還有CrypToadz by Gremplin、NounsNFT等。如果我們去coniun查看Mfers與藍籌項目的相互持有情況,可以發現Mfers的Mutual Holders排名前三的是Doodles、Mutant Ape Yacht Club,還有就是CrypToadz。由於是出自同一個技術開發團隊WestCoastNFT,Doodles持有的Mfers最多也不足為奇。
二級標題"Carry the flag on CC0"圖片描述
二級標題
Meme:從梗圖到NFT,再到CC0
NFT版稅運作機制:為什麼放棄權利會讓創作者賺到更多?其實,早在20年多年前就有CC0這個概念了。
在NFT尚未興起的古典互聯網時期,CC0更像是一種公益行為。在零邊際成本的複制中,圖片可以被自由地傳播。這種友好與開放的態度,帶給原創者的回報是非經濟性的,人們或許會努力尋找原圖出處,成為創作者在社交媒體上的followers,但更可能是對出處的漠不關心,這限制了CC0的作用範圍。
在非同質化代幣為jpeg規定了鏈上所有權的今天,jpeg圖片內容與區塊鏈智能合約產生了一種“嵌入關係”——通過合約編碼將規則自動執行的技術環境,對jpeg的營收來源產生了結構性的變革。在過去,沒有聲明CC0的內容如果被盜用,創作者將花費高昂的律師費來維護自己的版權,因為後者與收益直接掛鉤。
但NFT版稅設定,可以被編碼到智能合約中,在二次銷售中自動支付給創作者。數字藝術家通過自己的NFT作品在二級市場的流轉,取得持續性的收入。價值的發生環節下移了,發生在每一次交易轉手的過程中。每次創作者的NFT 在市場上售出,NFT 版稅都會為創作者提供銷售價格某個百分比的抽成,從2.5%至10%不等。
對於一個出色的NFT項目來說,這樣的價值環節下移產生的利潤是巨大的:例如BAYC與Azuki這樣的“藍籌項目”,二次版稅抽成已超過了一級收入。二級標題
二級標題
Figure 4 | Source:Unsplash
CC0更適合Meme類項目
儘管CC0會更好地促進NFT項目的傳播,但並不是所有的項目都會採用CC0。
為什麼呢?
為什麼呢?
為什麼呢?
對於BAYC和Azuki來說,品牌的傳播是依靠官方(即中心方)帶領持有NFT的用戶一同製作和擴散的。由於在視覺上本身不具備強meme屬性,它們在核心利益社區(即項目方和持有NFT的用戶)之外難以獲得天然的傳播度。
二級標題
二級標題
圖片描述
圖片描述
Figure 5 | Mfers 視覺特徵
Meme自我擴張的訴求與NFT本身的精緻與逼真程度成反比——不妨低頭看看我們微信裡收藏的熊貓頭,超清畫質的表情真的沒有高糊畫質好用,高糊甚至得到“包漿”的美譽——因此無數次傳播畫質被壓縮到最低的證明。
Mfers的簡易畫風會勾起我們兒時在課本空白處畫火柴人的記憶,不需要專業的繪畫技巧,人人皆可為之——如今,火柴人戴著耳機坐在桌前的狀態就是成年後的我們真實的寫照。 CC0許可敞開了創作大門,加密原生的年輕一代只需要回歸兒時的創作力與想像力,就能躍入meme的人聲鼎沸。
Meme類的NFT比藝術類、品牌類的NFT更傾向於使用CC0,因為Meme類NFT的火爆,非常依賴加密市場的FOMO情緒與社區的活躍,版權在這一過程中反而阻礙了Meme符號傳播與NFT交易。
二級標題
圖片描述
二級標題
CC0與大眾文化:回到費斯克與里夫金
最後,我想聊聊費斯克與里夫金。
費斯克是一位研究媒體的學者,他沿著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中積極受眾的路徑,發展出“生產性受眾觀”理論。
費斯克認為,在文化經濟中,流通過程並非貨幣的周轉,而是意義和快感的傳播。觀眾從商品的消費者轉變成生產者,即意義和快感的生產者。積極的受眾環境下,沒有消費者,只有意義的流通,意義是整個過程中的唯一要素。
有沒有覺得這說的很像當下的NFT市場?
NFT無疑是文化經濟的一種實現形式,NFT native是“大眾”。與meme化的Mfers相比,3D形式的NFT無疑是二次創作門檻最高的。由於“自己好像做不了什麼”,社區大眾只好把NFT的審美寄託在了專業的設計師與藝術家身上,把NFT的賦能寄託在了項目運營身上。
只有在CC0、meme化的NFT中,大眾才真正擺脫“內容接收者”的被動身份,而是自己成為意義與快感的生產者。
這一點至關重要。正如費斯克在《理解大眾文化》中指出:大眾文化是大眾創造的,而不是加在大眾身上的,它產生於內部或底層,而不是來自上方。在里夫金那裡,這就是“零邊際成本社會”中的協同共享模式,“生產性的受眾”是里夫金所謂的“以產消者構成的協同主義者”。在這一機制中,“產權讓位於開源共享,所有權讓位於訪問權,市場讓位於網絡”。
這讓人想起了web3理念對群眾創造力的尊重:Mirror.xyz的項目方不擁有內容的發布權、管理權,而是看到了web3工具組件的靈活性——流量經濟與長尾效應成為web2時代的“有限的遊戲”。
總結
總結
總結
《mfers: 喪文化,後亞文化下的web 3.0新部族》一文從“全球性的網絡文化思潮”、“後現代主義的觀念共鳴”等人文立場出發,探討了mfers的文化共同體內涵。本文則嘗試探討Meme、NFT、CC0三者共同創造的可能性:Mfers接過CC0的大旗,以meme為媒介標舉了一種叛逆式的NFT價值範式。
但正如費斯克所描述的,大眾具有“游牧式的主體性”,將在文化工業創造出來的層理間穿梭往來,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網絡流行文化總是經歷著快速的新陳代謝,梗圖與Meme會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出新的一茬。
而在文化層面,加密朋克的亞文化與對現實的現代主義“厭膩態度”,仍會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聯結起NFT native社區;在NFT價值結構層面,我們從Mfers身上看到了有別於傳統“項目方-消費者”的關係形式,也看到了加密敘事中的“公共價值”——在Mfers與3Landers之後,誰來執掌這面CC0的旗幟?